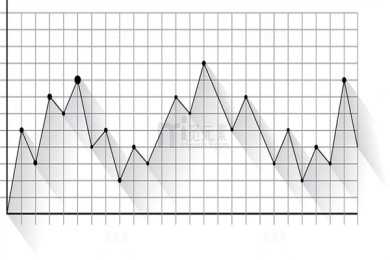古人作榜书是含糊不得的,更丝毫偷不得懒。“大字难于结密”,作榜书,稍有点画疏忽,便如盘中生蝇,很是涨眼;稍一放纵,又迹近俗字。因而,一般书家多不愿涉猎榜书。费纸费墨不说,实在讨不得半点机巧。
你想,门楣匾额,巨幛鸿幡,即便盈尺巨字,也须不差分毫。不然,悬于庙堂,或是游人如织的市镇店面,让人指指点点,点画之佞,格外涨眼,世人噱说,也着实叫书家闹心。不似当今书家,即便蝇头小楷,也可须臾之间放大成鸿篇巨制,全凭电脑作主。其实,古人也有放大之术,叫“烛光灯影投字法”。此法如何,没有见过,依我笨想,此术未必可靠,至少不精确,大小不可任人取用。如是,作榜书便是古之书家一大必备功课。
宋书尚意,除了给书法以浪漫主义翅翼外,也给了书法以广阔的容身之场所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中说,宋之前,宫中少有亭阁,宋则穷极奢侈,处处立亭建阁。有亭阁,亭堂楼阁便有名匾、楹联、屏风等设施,也便有了书画的去处。吴自牧《梦梁录》中记德寿宫说:“其宫中有森然楼阁,匾曰‘聚远’,屏风大书苏东坡诗‘赖有高楼能聚远,一时收拾付闲人’之句。其宫御四面游环庭馆,皆有名匾。”又记御圃中香月亭,说:“亭侧山后,环植梅花,亭中大书‘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’之句于照屏之上。”在此,亭阁即是展厅,尤喜榜书。
由此可见,宋之园林建筑的趣味与其书风的尚意倾向是合辙的。赖此,榜书便有了用武之地。如是,每至一地,苏东坡常常喜欢一人徜徉庙堂亭阁,多为欣赏字画。苏辙说:“余兄子瞻尝从事扶风。开元寺多古画,往往匹马入寺,循壁终日。”
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,宋时寺庙多方搜罗本朝墨迹,如东京大相国寺“大殿两廊皆国朝名公笔迹。”可以说,亭堂楼阁给榜书插上了翅翼,也蔚然成就了宋书之文化景观。因而,书家善榜书,便成了不可或缺的技艺。《铁围山丛谈》中记,蔡京就曾当着米芾、贺铸作了一回榜书表演:“元符末,鲁公自翰苑适祠,因东下,拟卜仪真居焉,徘徊久之,因艤舟亭下。米元章、贺方回来见,俄一恶客亦至,且曰:‘承旨书大字,举世无两。然某私意不过灯光烛影以成其大,不然,安得运笔如椽哉!’公哂曰:‘当对子作之也。’二君亦喜,俱曰:‘愿与观。’
公因命磨墨,时适有张两幅素者,左右传呼取公大笔来。即睹一笥有笔六七枝,大如椽臂,三人已愕然相视。公乃徐徐调笔而操之,顾谓客:‘欲何字耶?’恶客即拱而答:‘某愿作‘龟山’字可。’公一挥而成,莫不太息。”
观人作榜书,总令人“太息”。我虽未见“公”作书,然其作榜书之潇洒风采已跃然纸上,叫我“太息”不已。我也曾于网络上,见今之书家在体育场上作榜书,油头粉面,一身缟素,字尚未作,其粉墨登场之媚态,已令人喷笑。
诚然,不管你承认不承认,榜书确有其表演成分在。而榜书的风采,又多自其表演上出。笔舞如戟,墨渖淋漓,字走人蹈,翩然有姿,倘若配上古筝弦琴之乐,绝然一场龙飞凤舞的中国“秀”。
宋之何薳《春渚纪闻》中记了一则民间作榜书的事,全然勾勒出榜书之异趣:“政和二年,襄邑民因上元请紫姑神为戏,既书纸间,其字径丈。或问之曰:‘汝更能作大书否?’即书曰:‘请连粘襄表二百幅,当作一‘福’字。’或曰:‘纸易耳,安得许大笔也?’曰:‘请用麻皮十斤缚作,令径二尺许。墨浆以大器贮,备濡染也。’诸好事因集纸笔,就一富人走麦场,铺展聚观。神至,书云:‘请一人系笔于项。’其人不觉身之腾踔,往来场间,须臾字成,端丽如颜书。复取一小笔与纸角云:‘持往宣德门,卖钱五百文。’既而县以妖捕群集之人。大府闻之,取就鞠治,旋无他状,即具奏知。有旨,令就后苑再书验之,上皇为幸苑中临视。乃书一‘庆’字,与前书‘福’字大小相称,字体亦同,上皇大奇之。’”
因何不“奇”,作榜书,真真作出一奇异的小说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