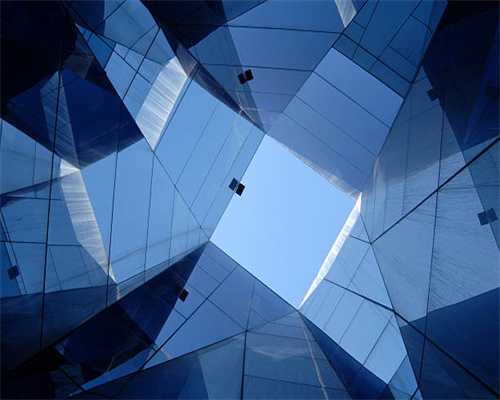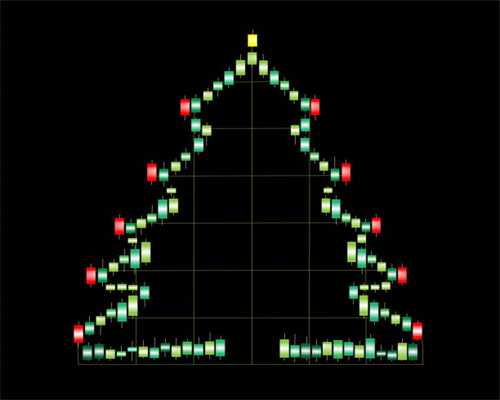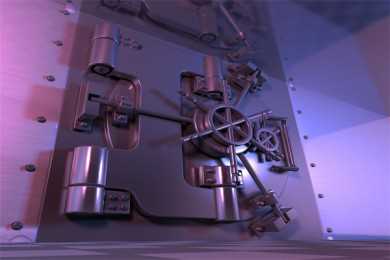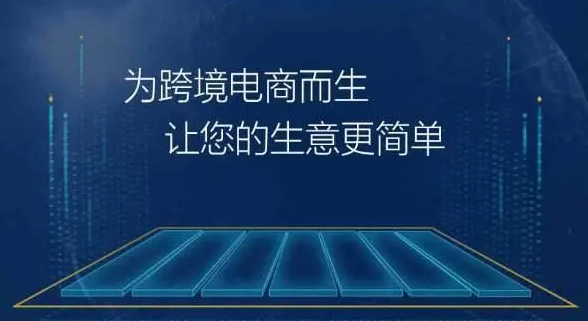赤县神州,天水府一海郡。八百里黑河浪滔滔,微风吹拂波光粼粼,带起大片芦苇摇晃作响。此时刚刚入秋,日头高挂却未有多少热气,又湿又冷的寒雾聚拢成团。不一会就浸透白启那身粗布单衣。他正站在一条小舢板上,提起昨天放下去的竹篾鱼笼,张望两眼,感到失落怎么又空了?这两天运气真不行。
鱼笼里头只有三四条的刀鳅,约莫半指来长,以及一只大碗便能装下的零碎河虾,根本没个正经的渔获。这要放在前世,白启都不好意思晒给其他的钓鱼佬,否则肯定得被冠上一个鱼苗猎手的耻辱名号。再撒一网乞求老天爷保佑。给口饭吃似是受不住黏糊糊的水气。
白启抹了把汗,脱去粗布短打露出尚算结实有力的一双臂膀。他双脚立定,身子猛然一拧甩出那张麻绳编织的旋网。呼的一声大网撒开像海碗倒扣,甫一入水就迅速沉下。白启用劲十分老练,动作也很利落。
若非十几岁的少年眉眼中仍然残存一些稚气,俨然老渔民是也。余下那一截牵绳被他稳稳拿住,反手绑在舢板尾端拖行出狭长水痕。撒网很耗气力,更吃技巧。十几来斤的大网单单抢起抛动就不容易,更别说要让摞成一团的渔网张开成圆。若无百来次的磨练想必很难做到忙活一通。
白启累得气喘吁吁,坐下摸出两个干巴巴的麦饼,就着瓦罐清水咀嚼起来。古代说的干粮原来是这个意思,确实又干又硬难以下咽。即便白启来到这方世界已经好一阵子,还是没能完全适应现今这种看不到头的苦日子。
我上辈子吃的麦饼里面有馅,会放梅干菜、萝卜丝、肉丁,两边刷油,一口下去喷香软嫩。白启使劲回想,腮帮子高高鼓起,用力啃咬。用麦粒煮熟压出来的干饼子简直与最糟糕的法棍无异,需要就着清水吞服不然铁定噎着。这年头大户人家都吃不起顿顿精米精面,至于把麦子碾成粉,和面发酵仔细烘烤做成那种名为"点心"的玩意儿实在太过奢侈。以黑河县渔家子白启的浅薄见识,当是州城府郡里头的老爷们才能享受得起。怪不得黑河县人人都想进城脱了贱户身,更好谋生路也更能吃饱饭。不然就只能看老天爷的脸色,白启囫囵吃掉两个麦饼,填饱辘辘饥肠,让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缓了一缓。
值得庆幸这具身子骨还行,而且有一把子力气,能够风速来雨力去,依靠打渔为生,艰难求活这些年,白启也算初步摸透置身的地方。此处唤作"黑河县",拢共占着五百里山道,八九十度非洲。俗话说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。之所以开得起百业营生,养得了十余万户全靠鱼栏、柴市、火窑。
这些县上首屈一指的好去处,因为提供得了做事的活计、谋生的生路又被称为米饭班子,意思是仰仗三大东家赏饭吃,大家才可以混个温饱,颇有种打工牛马对公司老板感恩戴德的荒唐感。原身之前就在鱼栏厮混,勉强挣得两口饭食。但只是堪堪糊口的艰难日子,终究不够稳妥好像白启身下那条小舢板,稍微大点的风浪拍打过来,人和船都要翻沉,贱户之身,只能操持贱业,出不了黑河县。
更进不了城,不靠着鱼栏、柴市、火窑,连温饱都难。白起摇头,很清楚当前处境鱼栏不是好心的善堂。如果长时间没大货上供,交不起抽成被夺走摊位。沦为无业游民,失去谋生门路也很常见。自打白启来到这里成为打渔人讨生活。
就饵闻过黑河县立着两条铁石般的规矩:一是不白养先人,二是不瞎讲道理。他听于蓝的老人讲,离这里十万八千里之远的中枢龙庭,把亿兆黎庶分为三六九等,最上为仙籍,官籍绝非白启所能接触得到。其次就是中下六户,鳝鱼,涧,涧,三,第六户合称九等。
像白启这样的渔民,没有田地,大多以舟为家,沿河而居,被唤作"白水郎""游艇子"据说,有的地方甚至不许他们上岸,更禁止通婚,可以讲。打渔人是位于百业营生,各种行当的鄙视链最底端,就比卖身为仆的农户做无偿苦工的义户稍好一些,逐水生活的渔家子,当然远不如地里刨食的农夫白起撒了撒嘴,毕竟土地才是产业,种田农耕才养得活人口,打渔、赶海,漂泊无依又岂能受待见。